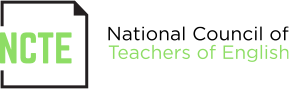本文由NCTE成员Deborah Appleman撰写。
当我还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时,我教过一些学生,我认为他们是在上大学和进监狱之间走钢丝。他们很聪明,但在学校里心不在焉。他们都是些有趣的、善良的年轻人,却经常惹上麻烦。他们的家庭生活通常很复杂。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上大学的材料,说实话,他们的大多数老师也不这么认为。
在我开始在监狱做志愿者之前,我的教学生涯——先是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后来是大学教授——使我与世隔绝,所以我只看到那些最后上了大学的学生。现在,在一所戒备森严的男性监狱里教了12年文学和写作之后,我看到了另一面,看到了那些没有被“麦田里的守望者”抓住的人,我们这些教师有时自以为是这样的人。
我认为每个学校老师都应该去当一段时间的监狱老师。虽然作为一名高中教师,我庆幸自己在帮助那些即将离开学校的学生时感到了紧迫感,但如果我更清楚地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这种紧迫感就会更强烈。
在我的班级里,有些学生在高中时被警察带走,有些学生在15岁时离家出走时犯罪,有些学生从寄养家庭到少年拘留所再到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有些学生已经从男孩成长为男人……在监狱里。
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判终身监禁,没有假释的可能,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判有罪。然而,他们是狂热的读者和作家,有着强烈的智力欲望,这在他们偶尔上过的高中、辍学或被开除的高中里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一天晚上,在监狱的文学导论课上,我正在传阅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桑尼的布鲁斯》(Sonny’s Blues)的诠释文章,我在齐克的课桌前停了下来,说:“这篇论文太棒了。你从哪学来这么写的?你在哪里上的高中?”
“90年代的南方高中。”
“我就在那儿,”我叫道。“我从没见过你。”
“这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上过课,”他说。“这太糟糕了,因为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可能就不会在这里了。”
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在想如果齐克有上过我的课。我真的相信一门有吸引力的英语课和一个感兴趣的老师会让一个有慈爱父母、容易抑郁、使用化学药品和同伴压力的城市青年的生活发生完全不同吗?当然不是。通往监禁的道路太复杂了,不能被一个积极的教育经历打断。此外,这种想法会危险地导致“老师是女英雄的心态”(例如,在书籍和电影中很流行)危险的思想)。在我看来,这不仅不现实;教师,尤其是白人女教师,把自己塑造成英雄或救世主是不尊重的,甚至是傲慢的,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学校里,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学生。
然而,我仍然对识字的力量抱有不可思议的幻想,它可以参与、改变甚至可能改变人生轨迹。我那些被监禁的作家也这么认为。
在我教的每一堂写作课上,我都要求学生撰写一篇作者陈述。以下是其中的一些摘录:
我写作是因为我别无选择。还有谁会成为我的声音,讲述我的故事,展示我的痛苦?谁来解释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败?谁来把我所学的教给他们呢?谁将激励?中美
我相信写作可以治愈最深的伤口,恢复破碎的灵魂。我的文字是我的全部,只要有人读我的文字,我就觉得自己还活着。约翰尼
我发现写作是一种实际的解放方式,需要努力工作和奉献,通过一个简单的任务,忍受一个压抑的环境。我把写作看作是一种与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群保持联系的方式。当我努力评估自己的价值,审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是什么把我带到了这里时,我的灵魂里一直在审计着。屁股的
阅读这篇博客的人更有可能在你的英语/语言艺术课堂中而不是在监狱的墙内产生改变。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些人被其他力量俘虏之前抓住他们的想象力和才能。如果我能知道我在监狱里教书时学到的东西就好了。
本博客的部分内容出现在监狱里的读写能力学习,诺顿出版社。
Deborah Appleman还将在2019年11月21日下午2:30 - 3:45举行的2019年NCTE年会上就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中断学校到监狱的管道:ELA教室中的共享探究。

黛博拉·阿普尔曼是卡尔顿学院霍利斯·l·卡斯维尔教育研究教授,曾任高中英语教师。她也是雪城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她是11本青少年识字书籍的作者/合著者;她最近的一本书,监狱里的读写能力学习,灵感来自于她最近的研究,在一所戒备森严的男子监狱教授大学水平的写作和文学课程。她和她被监禁的学生出版了一本创造性写作选集由内而外:给年轻人的信和其他写作。